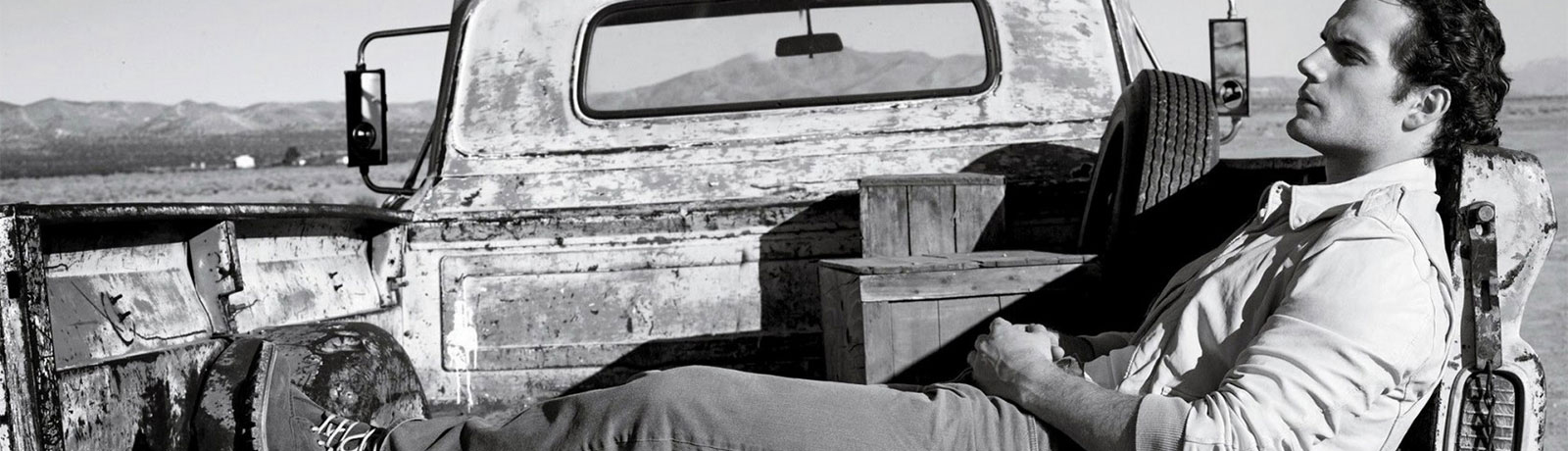北京市西城区图书馆内,“抗战老兵记忆”肖像作品展正在举行,150余张抗战老兵肖像照被精心装裱展出。时光不居,岁月如流,这些曾经历血与火洗礼的老兵已进入人生暮年,可一张张饱经沧桑的脸上,目光依然坚毅。他们面向镜头,或神情肃穆,或面露微笑,有人胸前还戴上了军功章或纪念章。
150余张抗战老兵肖像照,出自同一位摄影师之手。今年55岁的郭海鹏坚持20余年不计回报地为300多位抗战老兵、50多位抗美援朝志愿军老兵拍下肖像照,为老兵们留下珍贵的人生影像。
郭海鹏郭海鹏出生于北京一个军人之家,父亲和两个叔叔都在部队工作。他记得,小时候,父亲经常带他拜访赵朴初先生。“我们两家离得很近,步行15分钟就能到。”赵老常把自己抗战时的亲身经历当故事说给小海鹏听。
郭海鹏对赵朴初先生的英勇事迹早已熟稔于心:当年,淞沪会战爆发后,不少中国人逃进租界、露宿街头,成了无家可归的难民。赵老主动联系皖南新四军,又积极联系船只、筹集经费,突破日寇的封锁,分批把上千名青壮年难民从已是孤岛的上海送至新四军的队伍中支援抗战。赵老常对他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军人们除了胜利一无所求,为了胜利一无所惜。”
郭海鹏慢慢长大,身边当过八路军、新四军的老兵渐渐老去。学习摄影专业的他逐渐萌生了拍摄老兵的想法。一开始,他从周边认识的老兵开始拍。1997年北京新四军研究会成立,他参与其中,通过新四军老兵们的战友关系网认识了更多老兵,开始为他们的历史存档。
要拍好肖像照,先得学会“听故事”,才能够走进老兵的内心。
有一年秋天,郭海鹏带上背景布、补光灯、单反相机,驱车70公里来到河北廊坊八路军老战士杨敏学的住地。进了家门,他动作麻利地支起“移动照相馆”,一边布置场地,一边热络地和杨老拉家常。翻看老照片,郭海鹏得知,杨老18岁参加八路军,1940年8月参加了百团大战。
“抗战的时候,有什么让您开心的事儿吗?”“现在还有战友和您保持联系吗?”拍摄中,郭海鹏想方设法调动老兵的情绪,活跃气氛,等对方嘴角上扬、眉梢带笑,他便“咔嚓”一声按下快门。
拍摄完没多久,杨老就去世了,这也成了他最后的留影。
打动人心的拍摄场面不胜枚举。肖像展的一张照片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躺在病床上,右下角标记显示老人正是新四军老战士、《新四军军歌》曲作者何士德。郭海鹏回忆,当年,他和几位新四军老战士去协和医院探望何士德。“当时,何老已经卧床不起了,战友们围在他的床边,又一次唱起了《新四军军歌》给何老听。突然,何老伸出两只胳膊,在病床上开始打起拍子来……场面真让人动容!”
“拍老兵,捕捉眼神中的光非常重要,不同的眼光是不一样的故事。”每位老兵,郭海鹏会挑选10张左右照片,保存进电脑硬盘中,再标注上拍摄时间、老兵姓名。如果老兵或家属有需要,他还会精挑细选效果好的照片,冲洗出来送到老兵手里。
为老兵拍照,没人赞助,来回奔波搭路费不说,还占用了休息时间,但郭海鹏心甘情愿,“像在如人在,我想让后人记得他们的样子!”
长期接触中,老兵们刻在骨子里的军人作风令郭海鹏敬佩,“他们开会从来不迟到,跟过去作战攻山头一样准时;即便现在生活水平高了,他们的生活也都很朴素,从不奢侈浪费;他们的军装,一般都当作宝贝珍藏起来。”
“这是一场我们老战友的聚会!”今年8月24日,在妻女的搀扶下,101岁的新四军老战士陆锦荣来到“抗战老兵记忆”肖像作品展参观。一张张老战友的照片,勾起了陆老对过往的回忆。看到一幅照片,陆老的眼神逐渐凝重起来。他轻抚照片,指着里面的四个人,“现在除了我,他们三个都已经去世了。”这张照片,是2017年郭海鹏去陆锦荣家里拍的,照片里是陆锦荣与妻子的二哥、二嫂以及三哥,四人都是新四军。
“现在展出的这150余张老兵肖像中,有三分之二的人都已经去世了。”说到这儿,郭海鹏有些哽咽,“留给我们行动的时间不多了。”郭海鹏说,“20多年前,新四军研究会开会的时候,一屋子都是老兵,现在开会,几乎都是老兵后代了。”
2021年,郭海鹏将150余张老兵肖像摄影作品捐赠给抗战馆,向老兵致敬。今年,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他在西城区图书馆、中华世纪坛等地办起“抗战老兵记忆”肖像作品展,让历史不褪色,让岁月永留存。
如今,郭海鹏开始为更多抗美援朝志愿军老兵拍摄肖像照留念,也努力协调资源举办更多老兵肖像展。他希望能有更多人领略老兵们的风采,把红色基因代代传下去。